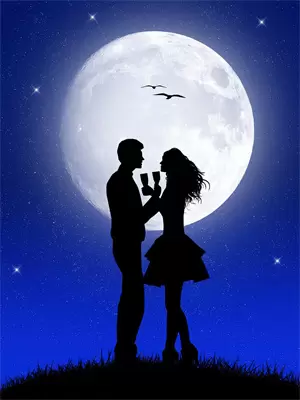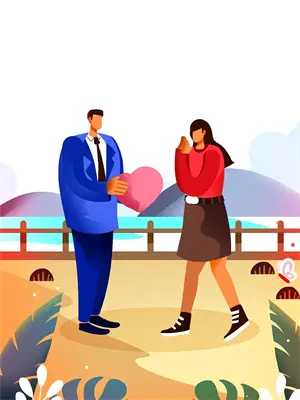
第一章云梦山初醒雨更急了。狂风卷着雨滴穿过茅屋的缝隙,打湿了我刚铺开的竹简。
那滴雨水正好晕在了一个“势”字上,墨迹散开,如同战场上瞬息万变的烟尘。
我盯着那团模糊的墨,忽然就笑了。天命?还是警示?连这云梦山的风雨,
都在催促我下笔了。我并非一开始就想写这样一本书。年少时,我也曾梦想辅佐明君,
立不世之功,像伊尹之于商汤,吕尚姜子牙之于文王。我遍览群书,揣摩天下大势,
自以为得了精髓。可看得越多,心却越冷。我见过太多所谓的英雄豪杰,
他们追求的不过是眼前的疆土与权柄,如同夏桀筑倾宫、商纣设酒池肉林,只图一世之快,
却看不见王朝基业下的裂痕,终将如九鼎迁于周室,江山易主乃是常态。真正的道,
不在朝堂的喧嚣里,而在天地运行的沉默中。它藏在星辰轨迹里,藏在四季更替里,
藏在溪流绕过山石的迂回里。我想写的,正是这沉默的法则,
这驱动万物、却又不显山露水的“枢机”。可如何下笔?
这比决定是否出山辅佐任何一位诸侯都难。若写得太直白,如同将利剑交于孩童之手,
恐遗祸苍生;若写得太晦涩,又怕后人如盲人摸象,不得要领。我提起笔,
感觉手中重若千钧,仿佛握着的不是笔,而是周武王伐纣时,在孟津举起的那杆大旗。
“先生,茶要凉了。”童子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。我挥挥手让他退下。此刻,
我需要绝对的孤独,就像当年大禹治水,三过家门而不入时的那份孤独。成就大事者,
必经孤独淬炼。我忽然想起了我的老师。他从不告诉我答案,
只是让我观察:观察蚂蚁如何搬运食物,观察鹰隼如何搏击长空,
观察市井商贾如何讨价还价。他说:“万物皆有其谋,万谋皆归于道。”那时我不全懂,
如今,当我要将这道诉诸笔端时,才明白其中深意。那么,就从这里开始吧。
我重新蘸饱了墨,手腕悬停,气息沉入丹田。雷声在山谷间滚荡,仿佛远古战鼓。
就在这一刹那,灵台一片清明。我落下了第一个字:“捭。”开启,阳的一面。
如同周武王在孟津会盟诸侯,公开讨伐无道。笔锋流转,第二个字随之而出:“阖。
”闭合,阴的一面。如同文王被囚羑里时,隐忍不发,暗中积蓄力量。这一捭一阖,
一开一合,便是天地阴阳运转的至理,是游说、谋略、兵法的总纲。
后世会如何解读这两个字?他们会用在庙堂,还是用在江湖?我已无法左右。我唯一能做的,
就是将这观察了数十年、思索了半生的天地之秘,用我的方式,记录下来。雨势渐歇,
东方露出了鱼肚白。烛火燃尽了最后一滴油脂,悄然熄灭。而我,王诩,
坐在云梦山的晨曦中,开始了这场与后世、也与自己内心的漫长对话。我知道,
这本名为《鬼谷子》的书,一旦开始,便再也无法回头。它将成为我存在过的证据,
也可能成为搅动未来风云的旋涡。但,道之所存,不得不言。
第二章龟甲上的预言晨光透过窗棂,洒在昨夜写就的“捭阖”二字上。墨迹已干,
可我的心绪却仍未平静。那滴晕开的雨水,让“势”字显得模糊而磅礴,仿佛在提醒我,
文字所能承载的,不过是大道的万分之一。童子收拾着狼藉的杯盏,
我则从箱笼深处翻出了一件旧物——一片残破的龟甲。边缘已被岁月磨得光滑,
但上面那纵横交错的裂纹,却依然清晰如昨。这是我少年时游历殷墟,
在一片荒芜的祭祀坑中偶然拾得的。那时,我对着日光端详它,只觉得那裂纹似曾相识,
像极了梦中见过的星图。今日再抚这龟甲,指尖触碰到那冰冷的刻痕,心中豁然开朗。
这哪里是普通的裂纹?这分明是“符言”,是天地通过灼烧的龟甲,
向殷商的贞人显示的征兆。我想起了那位生活在商周之际的传奇人物——箕子。相传,
在周武王伐纣的前夜,太师箕子曾用蓍草占卜,得“龙战于野,其血玄黄”之象。
当时众人皆惑,不知这“龙”所指为何,那“玄黄”之血又预示着什么。直到牧野之战,
苍穹变色,风雨如晦,战场上流淌的鲜血与泥泞混作一片玄黄,人们才恍然惊觉,
那卦象早已揭示了帝辛纣王与武王这两条“真龙”的殊死搏杀,以及一个王朝覆灭时,
天地同悲的惨烈。洞察先机,言符其实,这正是“符言”的精髓。 可洞察之后呢?
箕子看到了结局,却无法改变商纣的疯狂,只能披发佯狂,被囚为奴。这其中的无奈与抉择,
远比单纯的预言更为沉重。我提笔欲将这番感悟写入《符言篇》,可笔锋悬在半空,
竟久久无法落下。将天机说得太透,是福是祸?我眼前忽然浮现出在邯郸见过的那个老将军。
他一生历经七十余战,身上伤痕累累,如同我手中这片龟甲。长平一役,
他麾下的儿郎尽数被坑杀。我至今记得他站在残阳如血的城墙上,背影佝偂,
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:“王诩啊,你可知最好的兵法是什么?不是百战百胜,
而是不让战争发生。” 言毕,他便如一片枯叶,坠下了城墙。
“不让战争发生……” 我喃喃自语。这六个字,比任何奇谋诡计都更撼动我心。
我将其小心翼翼地融入正在撰写的《本经阴符七术》之中,试图阐述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,
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境界。然而,我删改了三遍。这样的道理太过沉重,也太过朴素。
世人追逐的是奇策,是妙计,是能立竿见影的权术。这般直指本源的大道,他们吞咽不下。
须得包裹上一层糖衣,一层源于生活、看似平常的糖衣,才能让这剂苦口良药,被世人接受。
就像这龟甲,若非承载着占卜的神圣,谁又会去仔细端详那看似杂乱无章的裂纹呢?
我放下笔,将龟甲置于案头。就让它作为这一章的见证吧。我写的不仅是谋略,
更是在这纷乱世事中,如何保全、如何洞察、如何在不争中取胜的智慧。只是这智慧,
需要后人用自己的经历去“灼烧”,方能显现出属于他们自己的“裂纹”与启示。窗外,
云开雾散,山色空濛。我知道,我要走的路,还很长。
第三章齐桓公的鱼盐昨夜下了一场春雪。清晨推开门,只见云梦山银装素裹,万籁俱寂。
童子欢喜,说是吉兆,瑞雪兆丰年。我却望着那被积雪悄然填补、抹平的山石沟壑,
心中想到的,却是“缝隙”。我正在写的,是《抵巇篇》。“巇”者,缝隙也。
山因微隙而崩,堤因蚁穴而溃,国因微瑕而亡。识得此“巇”,或弥补使其坚固,
或扩大使其崩塌,全在一心。道理我想得很明白,可落笔时,却总觉得隔了一层。
如何将这洞察祸患之先机的智慧,说得既透彻又不流于阴鸷?我搁下笔,信步走到院中。
积雪在脚下发出“咯吱”的声响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,无意间回头,
却见雪地上自己踩出的足迹,竟隐约连成了一个回环往复的图案,宛如八卦。我心中一动。
是了,天地万物,莫不存“巇”,亦莫不可用“巇”。而这雪后的寂静,
不正是为了让这世间的“缝隙”更容易被倾听吗?这寂静,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听到的,
关于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。那时齐桓公初登位,一心想着会盟诸侯,称霸天下。
他问管仲:“我们该练就怎样的强兵,才能让诸侯畏惧?” 管仲却答:“主公,
请先减轻关市的税收,让鱼盐之利更多地流通于民。” 桓公不解,
诸侯们更是嘲笑齐国重商轻农,舍本逐末。可结果呢?各国的黄金、布帛、谷物,
如同百川归海,悄无声息地流向临淄。诸侯们猛然发现,
自己的命脉已在不知不觉中被齐国握住。没有烽火连天,没有尸横遍野,霸业之基,
竟奠定于市井交易的锱铢之间。真正的权谋,何尝不是如此?它从不张扬于庙堂的宏论,
而是隐藏在鱼盐、关税、民心的细微褶皱里。 那看似不起眼的经济政策,
正是管仲找到的天下大势之“巇”,他轻轻一“抵”,便奠定了桓公九合诸侯的根基。
我快步回到案前,心中的滞涩豁然贯通。我重新提笔,在竹简上刻下:“巇始有朕,
可抵而塞,可抵而却,可抵而息,可抵而匿,可抵而得,此谓抵巇之理也。”写到这里,
我停住了。思绪飘到了许多年前,教导苏秦、张仪那两个小子的时候。
若我当时直接将这“抵巇”之理和盘托出,
告诉他们如何去发现各国君主的欲望之“巇”、国力之“巇”,他们或许会记下,
但绝不会刻骨铭心。正是我一次次将他们引入迷雾,让他们自己于困顿中摸索,
于碰撞中领悟,他们才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路。人,
总是更相信自己千辛万苦从迷雾中寻到的答案。雪,不知何时停了。阳光照在雪地上,
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我望着院子里那个被无意中踩出的八卦雪痕,心想,这天地间的阵法,
本就无处不在,只待一双能看见“缝隙”的眼睛罢了。《抵巇篇》的魂,终于抓住了。
第四章楚庄王的哑谜《抵巇篇》的竹简刚刚编缀完成,还带着新墨的清香,
一位年轻的士子便慕名寻上了云梦山。他风尘仆仆,眼神里却燃烧着急于建功立业的火焰。
见到我,他纳头便拜,开口便问:“弟子愿学先生纵横之术,求那一言可退百万师,
一语可安天下危的辩才!”我看着他,仿佛看到了许多年前,那些在诸侯间奔走呼号的身影。
他们舌绽莲花,他们权倾一时,可最终呢?苏秦身死,张仪飘零,那依靠口舌构建的联盟,
往往比朝露更加短暂。我没有直接回答他,只是指了指后山:“且去那里,听三月溪水声。
听明白了,再来见我。”他愕然,脸上写满了不解与失望,嘴唇动了动,
终究还是依言退下了。童子在一旁悄声问我:“先生,为何不直接点拨他一些诀窍?
”我摇了摇头。急火煮不出好羹,浮躁的心,听不进真正的道理。
这让我想起了楚庄王的故事。彼时,庄王即位三年,不理朝政,日夜饮酒作乐,
还下了道命令:“敢谏者死!” 举国上下都以为他是个昏君。殊不知,这三年里,
他并非沉湎酒色,而是在“不鸣不飞”的伪装下,冷眼旁观。他在等,
等所有的谄媚之臣原形毕露,等所有的忠贞之士浮出水面,
等所有的隐患与毒蛇都从阴暗的角落里爬出来。三年后,他一朝振翅,“一鸣惊人”,
罢黜奸佞,重用贤才,问鼎中原,成就霸业。有时候,沉默与蛰伏,
比任何激昂的言辞都更有力量。 这正如我在《反应篇》中所要阐述的:“欲闻其声,
反默;欲张反敛,欲取反与。” 你想倾听对方真实的想法,自己先要沉默;你想扩张,
反而要先收敛;你想获取,反而要先给予。那个年轻人只想“张”和“取”,
却不懂“敛”与“与”的妙处,更不懂倾听的智慧。傍晚,我独自修改《飞箝篇》。
所谓“飞箝”,便是以褒扬飞来笼络对方,以钳制箝来掌握主动。写着写着,
我忽然悟透了一层更深的意境:最高明的“飞箝”,并非外在的言辞技巧,
而是营造一种态势,让对方发自内心地认同你的观点,并以为那是他自己深思熟虑后的主意。
这就像昔年周公旦,制礼作乐。他没有用武力强迫诸侯服从,而是建立了一套煌煌典章,
一种行为规范,一种深入人心的高尚秩序。诸侯们自愿遵从,
以为这是自身修养与文明的体现,却不知已在无形中被纳入了周王朝的宏大体系之中。
这种温柔的束缚,比商纣王的炮烙酷刑,不知要高明、有力多少倍。“噗”的一声,
案上的烛火轻轻跳动了一下。我抬起头,听见山风正穿过屋外的竹林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那声音,不像是风在吹拂竹子,反倒像是无数古老的魂灵,借着这竹涛的低语,
在相互倾诉着那些未曾载入史册的智慧。那个去听溪水的年轻人,何时才能听懂,
这溪水要告诉他的,并非喧哗,而是深流呢?第五章九鼎的重量昨夜,
我被一个沉重的梦魇攫住了。在梦里,我并非王诩,而是化身为无数工匠中的一员,
围绕着熊熊燃烧的巨鼎。鼎身灼热,上面正被锤凿出九州的山川脉络、奇珍异兽。
那是大禹在会盟诸侯之后,收天下青铜所铸的九鼎。在梦中,
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那青铜冷却时的收缩之力,
仿佛将整个天下的山川河岳、万民生息都凝铸其中。醒来时,
我的掌心仍残留着那种沉甸甸的、冰冷而神圣的触感。我坐在榻上,良久未动。九鼎,
自夏传至商,由商传至周,它早已超越了礼器的范畴,成为“天命”与“王道”的象征。
它不言不语,却重若千钧,镇守在洛水之畔,令诸侯屏息。这,不就是“谋”的最高境界吗?
不谋一城一地之得失,而谋天下之舆图;不争一时一事之短长,而争万世之正统。
我步入书房,目光落在即将开始的《谋篇》竹简上。梦境的余味仍在心头萦绕。
真正的“大谋”,该有怎样的气魄与格局?我想起了商汤灭夏的故事。在鸣条之战前,
商汤与夏桀曾有十一场交锋,商汤皆败。若依常理,他早该一蹶不振。然而,这十一败,
如同十一次锤炼,既麻痹了暴虐的夏桀,也摸清了天下的形势,更淬炼了己方的意志。
直到第十二战,他看准时机,联合天下诸侯,一击而中,擒获夏桀于鸣条之野,
直接终结了一个时代。这十一败,非真败,乃是为那最后一擒所做的、最深远的“谋”。
我心中激荡,提笔在竹简上郑重刻下:“圣人谋之于阴,故曰神;成之于阳,故曰明。
”墨迹渗入竹纹的瞬间,我仿佛听见了一声来自历史深处的、悠长而沉重的叹息。
那是九鼎在洛水之畔,看着周室渐衰,诸侯不朝,
自知其象征的“天命”正在松动时所发出的叹息。“先生,”童子的声音在门外响起,
带着一丝不安,“最近山下总有几个黑衣人在林间转悠,已经好些日子了。
”我从那历史的叹息中回过神来,淡淡道:“不必理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