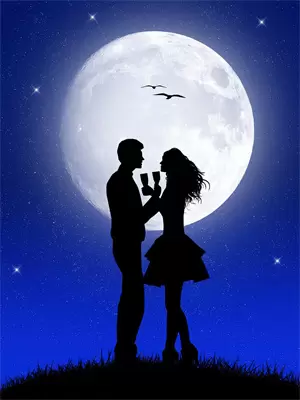林晚第一次见到陈砚之,是在腊月里雪意正浓的午后。梅花坞像被冻住的瓷瓶,
静卧在群山褶皱里,一场新雪刚歇,天地间裹着层蓬松的白,连风都慢了半拍,
怕惊散这满世界的素净。唯有坞口那片老梅林不肯服软,虬枝盘错如老者筋骨,
枝桠间缀满的红梅,艳得像燃着的火,在皑皑白雪里烧出惊心动魄的亮。
她怀里揣着母亲数了三遍的布票,硬邦邦的票证硌着心口,暖烘烘的。母亲说,
腊月扯块青布,赶在年前缝件新棉袄,让她过年时也能体面些。脚上的棉鞋是前年做的,
鞋底磨薄了,踩在积雪上,“咯吱——咯吱——”的声响在空荡的午后漫开,
像谁在轻轻拨弄冻弦。寒风裹着雪粒子,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,她缩了缩脖子,
把半张脸埋进洗得发白的棉袄领子里,只露出一双眼睛——那眼睛清凌凌的,
像梅枝上未化的雪,亮得能映出漫天飞絮。本想加快脚步穿过梅林,可目光刚扫过那片艳红,
就被梅树下的身影钉住了。是个青年,穿件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,料子看着是城里的细布,
却旧得没了光泽,袖口还磨出了毛边。他身姿挺拔,站在雪地里像株岩间青松,不歪不斜,
连落满肩头的雪花都没能压弯他半分。他没像过路人那样匆匆赶路,
反倒驻足在一株开得最盛的老梅下,袖口卷到小臂,露出截白皙的腕子,
腕骨清晰得像玉雕的棱。他正用指尖轻轻托着一枝被积雪压弯的梅枝,
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月光,连呼吸都放得极缓——仿佛那不是覆着雪的冷硬花枝,
而是捧在掌心的琉璃盏,稍重些就要碎裂。雪花还在落,沾在他乌黑柔软的发梢,
化成细水珠,又冻成小小的冰粒;落在他宽阔的肩头,积起薄薄一层白。可他浑然不觉,
眼里只有那枝梅,连眉梢都染着专注。风掠过梅林,卷着梅香绕着他转,他站在那里,
就像宣纸上晕开的淡墨,清寂里藏着动人心魄的隽秀,把这冰天雪地都衬成了水墨小品。
林晚的脚步蓦地顿住,心脏像被雪团狠狠砸中,“咚咚咚”地撞着胸腔,
声音大得她疑心会被对方听见。她其实早有耳闻——前几天去井边打水,
巷口的王婶拽着她胳膊,压低声音嚼舌根:“晚丫头,知道不?
村东头那间荒了好几年的旧私塾,来新先生了!听说是从省城来的,姓陈,叫陈砚之,
名字都文绉绉的,一看就是有学问的人!”当时她只当新鲜听,没往心里去,
却没想会在这梅林里撞见。她下意识地往后缩,闪身躲到一株粗壮的梅树后,
冰凉的树干贴着后背,才勉强压下些慌乱。她偷偷探出半张脸,目光又黏在了他身上。
雪光亮得晃眼,照得他侧脸线条格外清晰——鼻梁高挺,下颌线温和,连唇色都是偏淡的粉,
眉眼间拢着层书卷气的静,像刚从书里走出来的人。许是她的目光太沉,像落在他身上的雪,
积得厚了,他忽然若有所觉,缓缓转过头来。四目相对的瞬间,
林晚像被滚热的灯花溅到了手背,猛地一惊,慌忙低下头,连呼吸都忘了。
脸颊“唰”地烧起来,烫得吓人,连耳朵尖都在发烫。
她死死盯着自己棉鞋的鞋尖——鞋尖补了块黑布,针脚歪歪扭扭的,是她自己缝的。
手指无措地绞着棉袄衣角,粗糙的棉布磨着指腹,却丝毫压不住心里的乱。
平日里跟邻里说话还算伶俐的嘴,此刻像被浆糊粘住了,连句“路过”“抱歉”都说不出来,
只觉得喉咙发紧,连气都喘不匀。耳边传来积雪被踩压的“咯吱”声,很轻,却一步一步,
由远及近。他走过来了!林晚的手心瞬间沁出薄汗,黏腻腻地贴在棉袄上。她屏住呼吸,
身子往树后又缩了缩,像只受惊的小鹿,连指尖都在微微发抖。
直到一股淡淡的气息靠近——不是雪的冷,也不是梅的香,是墨香混着皂角的清冽,
还带着点书卷特有的干燥气息,温和地裹住了她。接着,一道嗓音在头顶响起,不高,
却像冬日里煨在小泥炉上的热茶,温温的,熨帖着耳朵,连带着心里的慌乱都被烘得软了些,
却又让她更无措。“姑娘,你也来赏梅?”林晚只觉得脖颈僵得像灌了铅,怎么也抬不起头。
她死死咬着下唇,从喉咙里挤出一个细若蚊蚋的“嗯”,轻得像片雪花,
刚飘出来就散在了风里。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停了片刻——那目光没有审视,
没有不耐烦,只有一丝淡淡的、带着好奇的探寻,像春风拂过水面,轻得不会留下痕迹。
过了会儿,那轻轻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,却是渐行渐远。林晚等到脚步声彻底听不见,
才敢慢慢抬起头。雪地里,只剩一道蓝色的背影,正朝着私塾的方向走,
长衫下摆在风里轻轻晃,划出道寂寥的弧。他方才托过的那枝梅花,
枝桠上的积雪“簌簌”落下,正好落在他留下的脚印里,白雪盖着浅痕,
很快就遮得差不多了,仿佛他从未来过,又像是她看花了眼,做了场短暂的梦。可林晚知道,
不是梦。那道清隽的身影,那句温和的问话,像一粒浸了水的种子,
悄无声息地落进了她心田的冻土里,连她自己都没察觉,已经开始悄悄扎根。那之后,
梅花坞的日子还是老样子——鸡叫三遍天亮,炊烟裹着饭香飘在巷子里,
女人们在井边洗衣说笑,男人们扛着锄头下地。可林晚的心里,却像被投入了一颗小石子,
漾开了圈不易察觉的涟漪。她还是那个勤快、话少的林晚,
照旧天不亮就起来帮母亲烧火、喂鸡鸭,白天缝补浆洗,傍晚去河边挑水。可有些东西,
确确实实不一样了。她开始有意无意地绕远路——去镇上扯线,
特意走经过私塾的那条;去后山拾柴,也选能望见私塾院墙的那条;甚至去巷口买酱油,
都要多绕半条街,就为了能从私塾门口多走一趟。那间旧私塾,早年也是书声琅琅的地方,
后来先生走了,就荒了,门前石阶长了青苔,窗纸破了洞,风一吹“哗啦”响,像哭。
如今陈砚之来了,才又有了点活气——院子里晒着他洗的衣裳,窗台上摆着个粗瓷碗,
偶尔还能看见他坐在门槛上看书,阳光落在他身上,连旧长衫都镀了层暖光。有时她路过,
能看见他在院子里劈柴。他显然没做过这种粗活,握着斧头的手有些生涩,斧头落下时,
力道偏了,只在木头上砍出个浅印。他皱着眉,调整了姿势再劈,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,
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微光。劈一会儿,他会直起身,用袖口擦汗,然后望着远处的山,
眼神飘得远,不知在想什么——是想城里的日子,还是在琢磨怎么教村里的孩子?
林晚猜不透,只觉得他望着山的样子,有点孤单,让她心里也跟着发涩。有时,
她会站在私塾墙外的老槐树下,隔着斑驳的土墙,听他讲课。村里愿意来读书的孩子不多,
就四五个,都是些皮实的半大孩子,上课总爱走神。可陈砚之从不发火,声音清亮又耐心,
讲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时,会举村里的例子,说张家婶子帮李家挑水,
说王家大爷给乞讨的人馒头;讲“床前明月光”时,会指着窗外的月亮,
让孩子们看月光怎么落在地上,像不像霜。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问“先生,
城里的月亮也这么圆吗?”“先生,床前真的会有霜吗?”他都笑着答,声音温温和和的,
像春风吹过麦田。那声音穿过冰冷的空气,钻进林晚的耳朵里,让她觉得,连这萧索的冬日,
都变得暖融融的。她靠在槐树上,听着他的声音,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树皮,
心里甜丝丝的——能这样远远听着,就很好了。可她从不敢靠近。每次远远望见他的身影,
或是听见他的声音,心就会漏跳半拍,像被人窥破了心事,慌忙躲到巷口的拐角,或是树后。
等他转身进了屋,脚步声没了,才敢慢慢探出头,望着私塾的门,
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——甜的是见着了他,哪怕只是个背影;涩的是,她跟他隔着太远,
他是城里来的先生,她是村里的姑娘,连跟他说句话的勇气都没有,只能像个影子,
偷偷跟着。这份隐秘的心思,像埋在心底的糖,甜,却不敢让人知道。她没跟母亲说,
没跟任何姐妹提,就自己揣着,像揣着块暖玉,捂在心里,成了平淡日子里唯一的亮色。
转眼到了正月,年味还没散,元宵的热闹又裹着甜香来了。梅花坞的元宵,
没有城里的花样多,就是母亲亲手包的糯米元宵,馅是炒香的花生、芝麻拌了糖,咬一口,
甜汁能流到心里。这天下午,母亲擦着一只竹编食盒,是早年外婆留下的,编得细密,
还带着点竹香。她把包好的元宵放进食盒,盖好盖子,递给林晚:“晚儿,
把这个给陈先生送去。他一个人来咱这穷地方,过年也没个人陪,怪可怜的。
让他尝尝咱家的元宵,也沾沾喜气。”林晚的手刚碰到食盒,心就猛地一跳,
像被什么攥紧了,连呼吸都乱了。去?还是不去?去了就能见到他,能跟他说话,
可一想到要跟他面对面,那点藏在心底的自卑和怯懦,
就像潮水似的涌上来——她穿的棉袄旧了,鞋尖补了块布,连话都说不利索,跟他站在一起,
多丢人啊。可不去,心里又像有只小猫在挠,痒得难受。她想再见见他,想听听他说话,
想看看他接到元宵时,会不会笑。最终,渴望还是压过了怯懦。她拎着食盒,手指因为用力,
指节泛白,几乎要把竹篾捏出印子。一路上,她都在心里演练——见到他,
要笑着说“陈先生,这是我娘让我送的元宵,您尝尝”;他要是道谢,就说“不客气,
先生您元宵安康”;声音要稳,不能抖,眼神不能飘,
要看着他的眼睛……她甚至想象了他的反应,他会笑着接过食盒,说“多谢林姑娘”,
声音还是那样温和。走到私塾门口,她停下脚步,深吸了好几口气,冷空气吸进肺里,
冻得她打了个哆嗦,却也让心里的慌乱压下去些。她抬手,
正要叩响那只铜门环——门环上锈迹斑斑,却被磨得发亮,
想来是他常摸——却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,不是他一个人。她的手,僵在了半空中。“砚之,
你真打算在这破地方待一辈子?”是个陌生的男声,带着城里人的口音,语气里满是不解,
还有点埋怨,“你在省城的工作多好啊,在教育局当科员,清闲又体面,工资还高。
何苦跑到这穷乡僻壤,教一群泥猴似的孩子?能有什么出息?”林晚的心,“咯噔”一下,
像掉进了冰窟窿,瞬间凉了。她像被施了定身法,脚挪不动,耳朵却不听使唤地,
紧紧贴向冰凉的木门缝隙。接着,是陈砚之的声音,比平时讲课的声音低些,却很稳,
带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:“这里的孩子需要老师。他们眼神里的光,
跟城里的孩子不一样——更亮,更真。而且……我喜欢这里的安静,梅花开的时候,很好看。
”“喜欢安静?”那陌生男声嗤笑了一声,带着点了然的戏谑,“我看你是找借口吧?
你当我不知道,你是为了躲家里的亲事!砚之,你都二十五了,不小了!苏家小姐我见过,
知书达理,模样又俊,家里跟你们家也是门当户对,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?难不成,
你真要在这村里耗着,耗到没人要?
”“亲事”“门当户对”“苏家小姐”——这几个词像冰锥,狠狠扎进林晚的心里,
疼得她喘不过气。原来……他是有婚约的。原来他来这偏僻的村子,不是喜欢这里的梅花,
不是想教孩子读书,只是为了躲婚。那他平日里的温和、平静,是不是都是装的?他心里,
是不是还想着城里的未婚妻,想着城里的日子?后面他们还说了什么,
林晚一个字也听不清了。巨大的失落像潮水,把她裹住,连呼吸都觉得困难。
她只觉得手脚冰凉,攥着食盒提梁的手,不受控制地发抖,食盒里的元宵跟着晃,
“砰砰”地撞着盒壁,像在嘲笑她——嘲笑她方才的演练,嘲笑她那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她像逃似的,猛地转过身,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。脚步虚浮,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地里,
好几次差点滑倒。来时觉得短的路,此刻却长得没有尽头。风刮在脸上,比之前更冷了,
像刀子割着肉,可她感觉不到——心里的疼,比身上的冷,重多了。回到家,
母亲见她脸色苍白,食盒原封不动地拎着,诧异地问:“怎么没送出去?陈先生不在家?
”林晚垂下眼睫,掩住眸底翻涌的泪意,声音低得像蚊子叫:“嗯……没人在,可能出去了。
”她把食盒放在灶台上,转身进了自己的小屋,关上门,背靠着门板,缓缓滑坐在地上。
眼泪终于忍不住,大颗大颗地滚落,砸在冰冷的衣襟上,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。她捂着脸,
肩膀不住地抖——原来那粒刚扎根的种子,还没发芽,就被一场倒春寒,冻得萎顿了。
那之后,林晚像变了个人。她不再绕远路经过私塾,甚至会特意避开——看见私塾的方向,
就赶紧拐弯;听见有人提陈砚之,就找借口走开。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,都投进了活计里,
像是要把自己累垮才甘心。天不亮,她就起来劈柴。院里那堆硬木,是父亲生前劈剩下的,
木头硬得很,平时都是母亲等村里的汉子帮忙。可林晚不让,她抢着劈,斧头落下,
震得她手臂发麻,虎口生疼,手上磨出了水泡,破了,流出血,她就找块布条缠上,接着劈。
母亲看着心疼,劝她歇会儿,她只摇头,说“没事,我有力气”。
她还主动包揽了喂猪、扫猪圈的活。猪圈里的气味熏人,连村里的汉子都嫌呛,
她却像闻不到似的,拎着猪食桶进去,一勺一勺地喂,扫猪圈时,动作麻利,一点不躲。
母亲说“这活脏,让你哥来”,她却说“哥要下地,我来就行”。晚上,
她坐在窗下缝补衣裳,就着昏暗的煤油灯,一针一线地缝。线拉得紧,扎得手疼,
她也不吭声,只是埋着头,缝了一件又一件——母亲的棉袄,哥的裤子,
甚至连家里的旧被单,都被她拆了重新缝。她不敢让自己闲下来,一闲下来,
那道蓝色的身影就会钻进脑海,带着梅香和墨香,让她心里一阵阵发疼。
她拼命告诉自己:别想了,没用的。他是城里来的先生,学识好,模样好,
将来是要回去娶苏家小姐的,过好日子的。而你呢?就是个生在梅花坞、长在梅花坞的村姑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