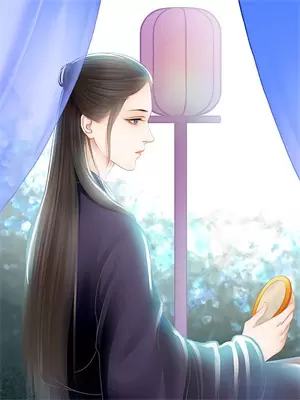周五的雨,带着一种不祥的执着,哗啦啦地冲刷着整个世界。我推开农发行沉重的玻璃门,
湿漉漉的伞在光洁的地板上留下一小滩水渍。大厅里异常安静,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。
前台无人,指示牌亮着,引导我去唯一开放的高柜窗口。防弹玻璃后面,是王惠子。
我认得她。来过几次,每次都会不经意地注意到这个漂亮的女孩。她不是那种惊艳夺目的美,
而是清秀温婉,像雨中的栀子花,安静地绽放。皮肤很白,眉眼细致,工作时微微抿着唇,
带着一种认真的可爱。业务很简单,很快就办好了。我瞥了一眼窗外,
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,天空阴沉得像一块湿透的灰布。看了看时间,
距离银行下班也就几分钟了。我叹了口气,准备冲进雨幕。“张哥。
”对讲机里传来她的声音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。我停住脚步,凑近麦克风:“怎么了?
”“门……门打不开了。”她指了指身后那扇厚重的、通往内部走廊的保险门。我愣了一下。
我们之间隔着坚不可摧的玻璃,我在相对自由的前厅,她却被困在了工作区。那扇保险门,
平时需要内部人员刷卡或密码才能开启。“别急,”我试图让声音听起来镇定,
“用对讲机呼一下你同事看看?”对讲机里只有沙沙的电流噪音,像某种不怀好意的低语,
没有任何人回应。我看到她拿出手机,手指飞快地滑动,然后抬起头,对我无奈地摇了摇头,
用口型说:“没信号。”一种诡异的寂静开始像雾气一样弥漫开来。太安静了,
除了单调的雨声,就是我和她之间隔着玻璃的、有些急促的呼吸声。银行不该这么安静,
尤其是在临近下班的时候。“你别紧张,”我再次开口,“我去后面找人帮你开门。
”她点了点头,眼神里流露出依赖和感激。我走出银行大厅,绕到建筑侧面的后院。
高大的黑色铁艺门紧闭着,门上的锁孔透着冰冷。平时在这里值守的保安不见了踪影。
雨点密集地打在我身上,冰冷刺骨。“有人吗?”我提高音量喊道,“开开门!
”只有雨声回应。雨水顺着我的头发流进脖颈,让我打了个寒颤。
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感攫住了我。不能再等了。我看了看铁门的结构,不算特别高,
顶部是装饰性的矛尖。我深吸一口气,抓住湿滑冰冷的铁条,用力攀了上去。翻身落地时,
裤腿和手肘都沾满了泥水,颇为狼狈。顾不得整理,我快步跑到办公楼一楼的走廊,
那扇厚重的保险门就在眼前。我隔着门上的小窗对里面喊:“王惠子!我去楼上喊人!
”办公楼里死一般寂静。我沿着楼梯快步向上,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产生回响,
显得格外突兀。二楼,财务部,门虚掩着,推开,里面空无一人,电脑屏幕是黑的,
桌面上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信贷部,同样空着。行长办公室,门关着,我敲了敲,没反应,
试着拧动门把手,开了,宽大的办公桌后,皮椅空荡荡地对着窗口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。
一种荒谬的、逐渐清晰的恐惧感爬上心头。三楼,四楼……每一层,每一个房间,
我都推开看了。没有人。一个人都没有。仿佛在某个瞬间,所有的人都凭空消失了。
茶水间的水壶还温着,似乎主人刚刚离开,但你就是找不到他。我跑回一楼,气喘吁吁,
雨水和冷汗混在一起。“楼上……楼上没人。”我对着门缝,
声音带着自己都能听出来的颤抖。“怎么可能?”王惠子的声音透过门传来,
充满了难以置信,“都快下班了,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?
李姐他们应该在收拾东西才对……”这不合常理。巨大的疑惑和恐惧让我们暂时忘记了处境。
下意识地,我伸手推了推那扇据说从外面绝对打不开的保险门。“咔哒。”一声轻响,门,
竟然应手而开。王惠子就站在门后,脸色苍白,嘴唇微微哆嗦,大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和茫然。
我们隔着一道突然变得毫无意义的门槛,面面相觑,都被这超现实的状况弄懵了。
“我们……是不是再找找看?也许他们在别的什么地方?”我提议,
主要是想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。她用力地点了点头,几乎是立刻靠近了我身边,
仿佛这样能获得一些安全感。我们又一次,更仔细地搜查了整个办公楼。
从地下室到顶层天台,每一个可能藏人的角落,储物间,甚至卫生间,我们都喊了,
推门看了。依旧是空无一人。回到院子门口的保安室,里面同样空空荡荡,
桌上的对讲机静静地躺着,椅子摆放得整整齐齐。我们再次尝试手机。无服务。无服务。
两个不同的运营商,结果完全相同。不是信号弱,是彻底的、毫无余地的“无服务”。
尝试拨打110、119,结果一样。我们被彻底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。
王惠子的身体开始明显地发抖,她看着我,眼圈泛红,声音带着压抑的哭腔:“张哥……我,
我好害怕。你能……你能送我回家吗?我想回家。”看着她脆弱的样子,
一种保护欲油然而生,暂时压过了我自己的恐惧。“好,我送你回家。”我语气坚定。
再次来到那扇院门前。我先翻过去,然后在外面接应她。她有些笨拙,我托着她的腰和手臂,
帮助她爬过来。她的身体很轻,在微微颤抖。落地时,我们俩都更湿了,像两只落汤鸡,
狼狈不堪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场。坐上我的车,我立刻发动,打开了暖风。
潮湿的空气里开始弥漫开一丝暖意。车子驶出农发行,拐上城市的主干道。雨刷器左右摆动,
刮开一片片水幕。街道的景象让我们刚刚稍缓的心再次沉入谷底。宽阔的马路上,
没有一辆行驶的汽车。路边停着的车排得整整齐齐,但里面没有人。人行道上空空荡荡,
店铺的霓虹灯依旧闪烁,但玻璃门后不见人影。红绿灯机械地变换着颜色,
指挥着不存在的车流。一座拥有数百万人口的繁华城市,此刻像一座被遗弃的巨大布景。
“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王惠子声音发颤,脸紧紧贴着车窗,向外张望。我没有答案。
只能紧握方向盘,朝着她家小区的方向开去。内心的不安像野草般疯长。就在这时,
车灯的光柱尽头,雨幕中,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。打着一把黑色的伞,站在路边,
似乎是在等车。我们俩几乎同时坐直了身体!“有人!”王惠子惊呼,
声音里带着绝处逢生的喜悦。然而,那喜悦甚至没能在脸上完全绽开,就凝固了。
就在我们的注视下,前方不到二十米的地方,那个打着伞的人影,没有任何过程,
像烟雾一样,倏地一下,凭空消失了。不是走开,不是躲起来,就是彻底的、瞬间的消失。
原地只剩下瓢泼的大雨,仿佛那个人从未存在过。“啊——!”王惠子短促地惊叫了一声,
双手捂住了嘴。我猛地踩下刹车,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尖叫。
车子剧烈晃动了一下,停在了人影消失的地方。我死死盯着那个位置,雨点砸在车顶上,
噼啪作响,像敲打着我们紧绷的神经。那里,什么都没有。恐惧,
此刻才真真切切地、如同冰冷的潮水般将我们彻底淹没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“没人”了,
这涉及到了无法理解的、违背常理的现象。我深吸几口气,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
重新启动车子,用更快的速度朝着她家的小区驶去。必须到一个熟悉的环境里,
必须确认一些什么。到达她住的小区门口,自动识别车牌的道闸杆毫无反应。
岗亭里空无一人。我按了几下喇叭,声音在寂静的小区里传得很远,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
“我……我走进去。”王惠子声音发抖地说。我从后备箱拿出唯一一把伞,撑开,
护着她走进小区。电梯运行正常,缓缓上升至八楼。走廊里安静得可怕。她掏出钥匙,
手抖得厉害,试了几次才对准锁孔。门开了。“爸?妈?”她试探着喊道,
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。没有人回答。房子里整洁干净,甚至飘着淡淡的饭菜香。
餐桌上摆着三副碗筷,还有几盘冒着微弱热气的菜。一切都显示,在不久之前,
这里还有人生活,有人在准备晚餐。但此刻,除了我们,空无一人。
王惠子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。她踉跄着冲进父母的卧室,又推开卫生间的门,
然后是自己的房间。每一个房间都是空的。“不见了……都不见了……”她喃喃自语,
身体顺着墙壁滑落,瘫坐在地上,眼泪无声地汹涌而出。我看着这一切,
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。不仅仅是她的父母,是整个世界的人,都消失了。
只留下我们两个。我走过去,蹲下身,想安慰她,却发现自己喉咙发紧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只能轻轻拍着她的背。她的哭声在寂静的房子里显得格外凄凉。不知过了多久,
她的哭声渐渐止住,变成低低的啜泣。她抬起头,泪眼婆娑地看着我:“张哥,
我们……怎么办?”“我们……再去别的地方看看。”我扶起她,
“也许……也许只是这片区域这样。”我们离开了她家,重新回到车上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,
我们像两个孤魂野鬼,开车在这座熟悉的城市里游荡。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,
平日里摩肩接踵,此刻空旷得可以听见自己脚步的回声。橱窗里的模特依旧摆着时尚的姿势,
却无人欣赏。火车站,候车大厅的座椅空荡荡,显示屏停止滚动。医院,急诊室的灯还亮着,
器械完好,病床上被褥凌乱,仿佛病人刚刚离开。警察局,
接警台前没有警察……所有的地方,灯火通明,设施完备,有些商店的门甚至敞开着,
欢迎着不存在的顾客。但,没有人。一个活人都没有。连一只老鼠,一只飞鸟,
甚至一只昆虫都看不见。整座城市,变成了一座精致而庞大的空城,
只有我和王惠子是两个意外的、被困在其中的活物。我们试图离开。
我找到最近的高速公路入口,通道敞开,ETC感应灯寂寞地亮着。我将油门踩到底,
车子在空旷的高速路上飞驰。雨已经停了,灰白色的天空下,道路笔直地伸向远方。
我们怀着渺茫的希望,期盼着穿过某个界限,就能重新回到那个喧闹的人间。开了很久,
久到油箱指针下降了一小格。当我看清前方路边的标志牌时,
一股彻骨的寒意和绝望瞬间冻结了我的血液——我们又回到了刚刚驶离的那个收费站。
熟悉的城市轮廓就在前方。我们绕了一个巨大的圈子,或者说,这个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循环,
我们根本无法离开。我将车停在路边,双手无力地垂下,额头抵在冰冷的方向盘上。
王惠子在一旁低声哭泣起来。我们明白了。不是世界毁灭了,
而是我们被从那个正常的世界里剥离了出来,
放逐到了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、静止的、无人的复制品之中。最初的几天,甚至几个星期,
是充斥着恐慌、崩溃和徒劳挣扎的。我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
我们疯狂地寻找任何可能的漏洞,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。
用固定电话拨打所有记得的号码,只有忙音。尝试打开收音机,搜索所有频段,
只有沙沙的噪音。找到有电脑的地方,网络连接标志上打着红色的叉。
我们甚至异想天开地试图破坏一些公共设施来引起“注意”,
但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维持着这里的“正常”,
损坏的东西会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悄然恢复原状。我们必须面对现实——我们出不去了。
至少,以我们目前能想到的方式,出不去。生存成了最具体的问题。幸运的是,
城市的一切基础设施都在诡异地正常运行。电力从未中断,自来水清澈流淌,
燃气灶一打就着。超市、商场、仓库里堆满了物资。而且,
我们很快发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事实——这个空间里的所有物品,都不会变质腐败。
超市里的蔬菜永远鲜嫩,水果不会腐烂,牛奶不会发酸,面包不会发霉,
冰箱成了多余的摆设。时间,在这些物品身上停滞了。
我们选了一家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公寓楼顶层的套房住了下来。用找到的工具或者说,
很多门根本就没锁打开了一间视野极佳的大户型。巨大的落地窗外,是寂静的城市全景,
白天车水马龙的景象如同幻觉,夜晚依旧灯火璀璨,却无人欣赏。开始,
我们之间还保持着一种礼貌而疏离的距离。
巨大的创伤和陌生的环境让我们都缩在自己的壳里。我们各自住在不同的卧室,
交流仅限于生存必需。但孤独和恐惧是最好的黏合剂。在绝对的寂静和空旷中,
人类本能地渴望同类的温暖,需要声音和触碰来确认自己的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