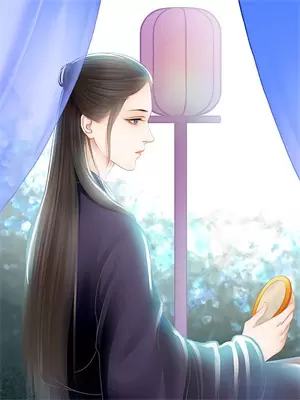# 第一章 失散的第七天## 1我醒来的时候,天还没亮。林子里弥漫着潮湿的雾气,像一层不肯揭开的纱。我的腿断了,不是那种"骨折了还能接"的断,是彻底断了——胫骨斜斜地穿出皮肉,断面白森森的,像一截被强行掰断的湿树枝。血已结成黑痂,稍一动,痂就裂开,温热的液体顺着脚踝爬进鞋底。我咬着自己的手背,不让自己出声。棚屋外的狗在嗅门缝,铁链"哗啦"一声,我就知道它闻见了血腥。那畜生叫"老黑",吃人吃惯了,眼睛是灰绿色的,夜里会发光。它看我,向来像看一块会走路的肉。## 2棚屋只有三步长、两步宽,原木缝隙里灌了泥浆,还是漏风。地面铺着一层潮得发黑的稻草,踩上去"咕唧"作响,像踩在腐烂的肺上。墙角有一只塑料桶,是我大小便的地方。桶沿永远湿黏,爬着细小的白虫。我数着缝隙里透进来的光,从一条、两条,到灰白一片——第七次被关在这里的早晨。七天前,我还背着三十升的远足包,举着自拍杆,在旅行团的大旗后面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吵架那夜,我把男友微信拉进黑名单,关机,买了一张单程车票,只为证明"没有你我也可以很好"。现在才知道,世界很大,大到可以一口把人吞了,连骨头都不吐。## 3第一次逃跑是在进山第三天。我们团三十人,走的是所谓"野人考察线"。导游阿凯说,这条线"手机没信号,风景原始到像回到白垩纪"。我故意落在队尾,想拍一株罕见的珙桐,再抬头,前面的人已转过山嘴。我喊了两声,密林把声音吞得干干净净。我打开地图APP,屏幕空白,只剩一个孤独的小蓝点。那时我还不慌,自认为方向感不错,便顺着山脊往下走,打算抄近路到营地。太阳西沉时,我看见了炊烟——不是营地,是山坳里的村子。村口有男人蹲在溪边磨刀,听见脚步声抬头,冲我笑,一口被烟熏黄的牙。"你走丢了?"他问,把刀背在裤腿上抹了抹。我点头,喉咙干涩。"进来喝口水,我帮你联系导游。"他指了指身后,竹楼、炊烟、玩耍的孩子,一切看起来那么正常,像纪录片里的少数民族村落。我跟他进了村,再也没走出来。## 4夜里他们摆了长桌宴,腊肉、土酒、自酿玉米白。我举杯抿了一口,酒里带着微苦的草药味。十分钟后,天地旋转,我软成泥。再醒来,已被反绑在黑暗的木屋里。我记得头顶的房梁有一道裂缝,像闪电;记得煤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,影子比人高大,像山鬼。三个男人轮流进来。我咬其中一人的耳朵,血腥味冲到脑门,换来第一顿毒打——肋骨断了,左耳被撕掉半块软骨。后来我学乖了,不挣扎,只数数。数梁上的裂缝,数煤油灯里浮沉的蛾子,数自己还剩多少尊严。## 5第二次逃跑是在一个雨夜。我装病,说肚子痛,要上厕所。门口守着的妇人"阿玉"开了锁,她腿瘸,走路拖步。我趁她转身,抡起粪桶砸在她后脑,桶裂,腥臭的粪水溅了我一身。我光着脚冲进雨里,踩着泥、草根、碎石,一路往山脊跑。闪电劈开夜空,我看见自己影子像鬼。跑不出五百米,他们放狗。老黑扑上来,牙齿陷进小腿,我听见"咔嚓"一声,不知道是木头断了,还是骨头断了。它拖着我往回拽,像拖一只死鹿。后面的人举着火把赶到,一脚踹在我胸口,世界翻了个面,雨点直接砸进瞳孔。那一夜,他们把我吊在柴房,用铁丝抽。抽一下问一句:"还跑不?"我昏过去,又被盐水泼醒。左腿就是在那时被打断的——木棒抡在膝盖外侧,"咯啦"像干树枝折断,疼痛像滚烫的铁丝顺着血管往上缠,直缠到心口。## 6第三次逃跑,是装疯。我学狗叫,吃生米,用指甲挠墙,把额头往地上磕,血糊住眼睛。他们起初不信,拿烟头烫我手臂,我咯咯笑,笑得口水滴到胸口。几天后,他们开始嘀咕:"这女娃怕是真疯了。"疯子没人愿意碰,看守松懈。我趁晌午换岗,从后窗爬出,拖着断腿,用两手扒地,一寸寸挪到林边。林子里有风,有鸟,有自由的味道。我抓住一棵小桦树想站起来,腿一软,整个人滚下山沟。沟底是厚厚的腐叶,像一张吸饱水的毯子,我陷进去,爬不动,也听不见追喊,只看见天一点点黑。我以为自己终于逃掉了,甚至笑出了声。可笑声未落,头顶出现一圈火把,像一串坠落的星。他们站在沟沿,俯视我,脸被火光照得通红,像阎王殿的小鬼。有人滑下来,揪住我头发往上拖。我听见自己头皮被撕离的"哧啦"声,像湿布被撕开。那晚之后,他们把我扔进这个棚屋,门上多了一把铁锁,墙外多了一条狗。## 7此刻,天已大亮。阳光从缝隙漏进来,像一排细小的银针,扎在我脸上。我侧过身,把腿平放,尽量不让断骨再戳破新长出的嫩肉。棚屋外的脚步声由远及近,门板被踹了一脚,灰尘簌簌落下。"吃!"一个瓷碗被推进来,里面是发馊的玉米糊,表面漂着一只死苍蝇。我爬过去,端起碗,先舔掉苍蝇,再一口一口喝。馊味冲鼻,我忍吐,忍泪,忍恨。我要把每一口淀粉都咽进胃里,化成热量,化成力气,化成下一次——是的,还有下一次——逃跑的资本。因为我知道,山外有人,或许正翻遍每一座岭、每一条沟,找我。因为我还活着。只要活着,故事就还没完。# 第二章
没有野人## 一棚屋外的雾像一张湿透的宣纸,阳光拼命戳也戳不破。我捧着那只豁口的瓷碗,把最后一滴馊玉米糊刮进嘴里,听见铁链“哗啦”一声——老黑被解开了。门缝投下一道影子,扁担那么长。“出来。”是阿玉的声音,嗓子被烟熏得发干。我爬出去。断腿拖在身后,像一条不属于我的附件,着地便钻心地疼。阿玉嫌我慢,伸手揪住我后领,连拖带提。老黑跟在后面,鼻子蹭到我脚背,呼出的热气带着腐肉的腥甜。屋外是村子的早晨。竹楼依山错落,炊烟爬上黑瓦,又被风撕碎;溪边有女人捶衣,棒槌声空洞,像敲在棺材板上。田埂上奔跑的孩子赤着脚,脚踝戴着银铃,叮铃铃——每一声都在提醒我:你曾是自由的。我数过,这个“麻湾村”总共七十六个人,其中女人三十一名,能说话的不超过十个。其余的不是疯就是哑,再不就是还没长牙的婴孩。## 二他们把我拖到晒谷场。谷场中央竖着一根木桩,桩上拴着一个人——不,是“人形”。乱发垂到胸口,发隙里露出一双灰白的眼珠,瞳孔缩成针尖,不知是怕光还是怕人。他右腿齐膝而断,创面裹着脏到发硬的布,布外爬满绿头苍蝇。“新来的,”阿玉用扁担敲敲我后脑,“看清楚了,这就是逃跑的下场。”那“人形”似乎听见“逃跑”二字,浑身一抖,喉咙里发出“咯咯”声,却吐不出一句完整话。阿玉笑,露出参差犬齿:“药灌多了,声带烧坏。不过放心,他还听得懂。”她让我跪在旁边看。两个男人抬来一只铁皮桶,桶里盛着半凝的猪血,表面结了一层黑膜。他们把桶放到断腿人面前,解开他一只手。那人像被烫到似的猛缩,却被抓住头发往下一按——整张脸浸进猪血。“赏你的,补铁。”男人笑。咕嘟咕嘟,气泡翻上来,破裂。我别过脸,一阵干呕。阿玉掐住我下巴,把我扭回去:“再吐就让你舔干净。”十几秒后,那人被提起,脸上覆着一层暗红面具,只露出转动的眼白。他喘,血珠顺着下巴滴到胸口,像给肮脏的布又刷了一层漆。我认出他——旅行团里的北京小伙,曾借我充电宝。那时他嚷着要拍“野人脚印”,如今他自己成了被展览的“兽”。## 三猪血仪式结束,谷场逐渐散去人。阿玉把我拎到溪边,扔进浅滩。“把自己洗干净,晚上有客。”她丢下一截肥皂,走了。水冷得像刀,我咬牙脱衣。腿伤浸水瞬间,疼得眼前炸黑,我咬臂逼自己别晕——再晕一次,他们会把我当死狗拖回去。肥皂是工业香精味,冲鼻的茉莉。我搓到皮肤发红,仍觉得血腥味嵌进毛孔。上游有女人也在洗澡,她们背对我,肩胛骨凸出,像两扇要破皮而出的翅膀。没人说话,只有水流和风声。我忽然听见哼唱——“哟——嗬——嗬——”调子拖得极长,尾音颤抖,像哭又像招魂。我抬头,对岸林子里闪过一个影子,高大,披乱发,全身披挂树枝。只一秒,便没入雾中。我僵住。那就是“野人”——被刻意制造、豢养、展出的“标本”。## 四傍晚,我被人抬进竹楼底层。屋里点松明,火舌舔着屋顶的熏肉,油滴落,“滋啦”一声。长桌后坐着村支书麻贵,四十几岁,脸瘦而黄,眼里却燃着与松明一样的火。“林小姐,又见面。”他普通话标准,像当过老师。我第一次被抓时,他坐在人群里,用指甲锉磨指甲,边看边打分。我垂眼,湿漉漉的头发滴水,在地板上洇出深色圆斑。“我麻湾向来好客,”他抿一口玉米酒,“尤其欢迎城里人。你们有文化,有朋友圈,一吆喝就是流量。”他抬手,旁边的人递上一只相机——我的,限量款,防摔防水。他打开相册,滑过我拍的云海、珙桐、集体合照,最后停在一帧视频:镜头晃动,对准村口石碑,“麻湾”二字清晰。“拍得不错。”他笑,“可惜配文要是‘失踪地’,就更炸了。”我嗓子发干:“你想怎样?”“简单。给你男朋友报平安,说你在深山找到‘野人’,兴奋得不行,想再待一个月。语气要娇,要真。”他把相机推到我面前,“录。”我沉默。麻贵抬下巴,旁边壮汉扯住我断腿,往上一折——世界瞬间被白光充满。我惨叫,声音像钝铁片刮玻璃。“录。”麻贵重复,语气像在吩咐添饭。我颤抖地举起相机,对准自己。屏幕里出现一张苍白的脸,眼窝青黑,嘴唇干裂。我努力弯嘴角,却扯出比哭还难看的表情。“……阿执,”我叫男友名字,声音嘶哑,“我……我看到了野人,太震撼了……我想再留一段,别担心……”说到“担心”二字,泪滚下来,砸在镜头上。麻贵伸手按下停止键,满意地叹了口气。“合作愉快。”他起身,俯到我耳边,“记住,麻湾没有野人,只有演员。谁不敬业,谁就下台。”## 五夜里,我被锁进谷仓。仓内堆满玉米棒,空气里浮着霉尘。月光从屋顶破洞漏下,像一根倾斜的银线。我蜷缩在玉米堆上,腿肿到发亮,皮肤撑得透明,似乎一戳即破。远处传来婴儿的啼哭,断断续续,像被什么掐住脖子。我忽然意识到,这村子最大的恐怖不是殴打、强奸、断腿,而是——它把恶日常化。恶被炊烟、童谣、玉米酒包裹,变成一日三餐,变成孩子的银铃,变成他们嘴里“老祖宗的规矩”。我抱紧自己,指甲掐进掌心。我要记住疼痛,记住仇恨,记住每一张脸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出去,我要让这日常,彻底崩塌。## 六月光移走,谷仓陷入漆黑。我听见老鼠啃玉米的“嚓嚓”声,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,听见心跳——一下,一下,像远处传来的鼓。忽然,门缝下有动静。我屏息。极轻的脚步,像赤足踏地。随后,一小团黑影钻进来——是个孩子,不超过六岁,头发剃得参差不齐,眼睛大得与脸不成比例。他蹲到我面前,伸出脏兮兮的小手,掌心躺着一块被捏扁的奶糖——“大白兔”,糖纸皱得发白。我不敢接。他把糖放在我掌心,又指自己喉咙,做出“嘘”的手势,转身跑了出去,像只灵巧的夜猫。我攥紧糖,糖纸棱角刺进皮肤。这是被囚以来,第一次收到不带条件的“给予”。黑暗中,我剥掉糖纸,把糖含进嘴里。甜味在舌尖炸开,像一粒极小的火,倔强地亮在漫无边际的夜里。我告诉自己:看,他们还没完全胜利。只要还有一点甜,我就有机会,把苦,全部还回去。# 第三章
疯女人## 一
暗渠里的水滴暗室无窗,时间像煤油灯罩里那圈昏黄,凝滞不动。我趴在床底,耳朵紧贴潮湿的泥地,听外面每一粒脚步声。铁门"哐啷"一声,程述被架回来,左臂软得像空布袋,袖口沾着新鲜血迹。她却在笑,牙齿被血染得通红,像含着一朵野蛮的花。"麻贵的手腕,"她用气音说,"我撕下一块肉,咽了。"她瘫坐在床沿,示意我扶她。我拖着断腿挪过去,她把额头抵在我肩上,重量一点点沉下来,像要把二十年的屈辱都借我体温蒸干。我闻到她发间陈年的土腥味,也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——那是她早年实验室的记忆,被皮肤牢牢锁住,竟没被岁月卷走。"地图......"她右手颤抖,把那块布片展开。布是从她内衣缝拆下来的旧纱布,经纬交错,用血和泥画成一张微观地形图:祠堂、暗渠、悬崖、河谷,一个指甲大的箭头指向崖底,旁边写着两个字——"河口"。我喉咙发紧:"我背你,一起。"她摇头,指尖划过我断腿外侧的伤口,疼得我抽气,她却笑得温柔:"别逞强。你一个人,是火苗;背我,就是两捆湿柴,谁都走不了。"灯芯"噗"地爆花,光影在她脸上游走,照出纵横交错的皱纹——那些皱纹不是岁月,是夜以继日的恨。她抬手,从发髻深处摸出一根磨到发亮的自行车辐条,顶端被敲扁,成了微型起子。"暗渠尽头的石板,用这撬。撬不动就拧——石板角有废弃的铜线,拧断即开。"她把辐条塞进我掌心,"我留在这,给你断后。"## 二
她的"断后"程述所谓的"断后",是继续扮演疯女人,而且升级成"狂犬症"——让全村相信她随时会咬人、会传染,从而把搜捕重点锁在她身上。她让我用尖石在她额头划一道"十"字伤,再撒灶灰,造成感染溃烂的假象。我手抖,划浅了,她抓住我手腕用力一拉,血珠立刻涌出,像打开的红墨水瓶。"再狠一点,"她嘶声笑,"做戏做全套。"血顺鼻梁滴到嘴角,她舔了舔,轻声说:"二十年前,我进来那天,也流血,只是那时我哭;今天流血,我笑。你记住,同样的伤口,可以哭,也可以笑,全看你拿它当什么。"我咬唇,不让自己哭。她却像看透:"别忍,眼泪是盐,浇在伤口上,疼才真,恨才深。"## 三
暗渠第三天亥时,鼓声停歇,村子沉入酒醉的鼾声。程述用右臂抱住我,像把最后的电量灌进我身体:"明晚'封山祭',所有人聚在祠堂前跳舞,暗渠口没人守。你趁子时落潮,水声大,脚步掩得住。"她递给我一只用猪尿囊缝制的小袋,里面装着火石、干菌粉、五颗野山椒,"火石取暖,菌粉遇水能膨胀,可充饥;辣椒抹嘴唇,保持清醒。"我点头,把布地图、辐条、小袋全绑在腰间,再用草绳缠死。她忽然伸手捧住我的脸,额头抵额头,声音低到像从地底传来:"要是河口干涸,就顺崖缝往北走,那里有片金丝猴投食点,保护站的人会巡查。记住——见到穿迷彩服的人,先喊'程述',再报自己名字,那是我的暗号。"我喉咙发硬:"我一定回来接你。"她笑,眼角却渗出泪:"不用接,只要你能出去,我就在这破祠堂里,每天撕他们一块肉,等你带人端锅。"## 四
疯子的狂欢第四日,天没亮,程述开始"发病"。她先是在暗室里用头撞墙,"咚咚"像敲鼓,把看守引进去;又咬人手腕,血溅一墙。麻贵暴怒,亲自带人把她拖到晒谷场,用竹杠压住四肢,拿撬棍撬开牙关,灌"哑药"升级版。我被人押在廊柱下旁观,心脏像要裂。程述却在大口灌药间隙,抬眼找我,目光穿过人群,像穿过二十年浓稠黑暗,落在我脸上——极轻,极亮。她趁麻贵不备,猛地合嘴,撬棍滑脱,反震力把麻贵虎口震裂。鲜血滴在她胸口,她含混地笑,血水从嘴角溢出,像吐出一场迟到的春雨。那一刻,我知道她赢了:所有人都会相信,这个疯女人危险到必须锁进祠堂重枷,再没空留意我这只"温顺的小羊羔"。## 五
子时之前深夜,我被反绑在谷仓柱子上,看守是老黑的主人——麻三,酒糟鼻,呼噜声赛过发动机。我一点点磨断草绳,掌心皮肉被勒翻,却不敢停顿。子时钟响,我爬出谷仓,拖着断腿,沿墙根阴影挪到祠堂后墙。月光被云遮住,只剩星辉,像撒落的盐。我找到那块松动的青石板——程述用指甲在边缘刻了极浅的"×"。我用辐条插进缝隙,一点点拧撬。石板发出"嚓——"的呻吟,像老人临终的喉音。汗水流进眼角,世界咸得发苦。突然,"咔嗒"一声,石板掀起半掌宽,一股阴冷湿气扑面,带着鼠粪和青苔的味道。我深吸一口气,把身体塞进黑暗,像把一封信塞进邮筒——寄给未知,也寄给必达。## 六
回声暗渠比想象狭窄,仅容匍匐。水淹到肘弯,冰冷如针。我向前爬,每挪一步,就用辐条敲一下石壁,"叮——"金属声在黑暗里传出很远,像给程述发信号:我走了,别担心。爬到三十步,身后忽然传来"咚!咚!"——祠堂鼓点暴起,接着是嘈杂人声、狗吠、铜锣。我知道,程述的"狂犬症"发作了,全村去围猎她。我咬住嘴唇,把呜咽咽回肚子,继续爬。水声渐大,暗渠尽头出现一块亮斑——月光透过栅格,像一把银梯,从高处垂到水面。我攀住栅格,用辐条拼命拧。铜锈屑落进眼睛,杀得生疼,却不敢停。忽然,"嘣"一声脆响,栅格松脱,我随水流冲下——整个人被抛进夜空,又坠入一条湍急山溪。冷水瞬间封住口鼻,我拼命蹬腿,断骨像被重锤,疼得眼前炸白光。但我没松手,一直攥紧那根辐条——那是程述的骨头,也是我的脊梁。浮出水面那一刻,我听见风穿过林梢,发出低沉的"呜——",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,喊一个名字。# 第四章
血鼓与暗河## 一
跌落的月亮我被暗河甩出洞口,像一枚被吐掉的果核,坠入山溪。水比想象更急,瞬间把我卷到三米下的回水湾。断腿在冰冷里麻木,疼得发亮,我死死攥住辐条,像攥着最后一根神经。月光打在浪尖,碎成万片银鳞。我抬头,看见悬崖上的祠堂——火光明明灭灭,鼓声"咚咚"正急,像一颗被剖开的心脏,把血溅进夜空。那一定是程述制造的混乱。火与鼓,是她给我的送别礼。我咬紧山椒,辣味像刀,把昏厥逼退,然后顺着水流往北划。布地图写得很清楚:沿溪三里,有一处金丝猴投食点,每天天亮前护林员会巡山。我必须在潮气未散前赶到。## 二
水中坟场溪流转弯,水面突然浮满黑色暗影——一具具"野人"标本,被铁链锁在沉木上,像水下墓碑。浪涌过来,尸体半沉半浮,乱发缠着树枝,眼球早被鱼啄空。我差点呕吐,辣椒混着胃酸卡在喉咙。那些曾是活人:游客、向导、护林员,甚至外地记者。麻湾把失败的"演员"扔进这里,任暗流把他们做成不腐的警示牌。我伸手拨开一具挡路的尸体,铁链"哗啦"作响,腕骨上还挂着半块手表——表盘停在某年某月某日的子夜。那一刻,我听见自己的心脏"咚"一声,像替它重新跳动了。我低声说:"我带你走。"然后把那块表撸下,套进自己手腕,表带冷得像环冰。## 三
火与鼓的背面鼓声忽然乱了,祠堂方向升起红旗状的火光。风把焦糊味送下河谷,我意识到:程述点燃了祠堂侧廊的松明仓。那是麻湾百年来最神圣的地方——火种与族谱共存。火借风势,眨眼爬上黑瓦。远远看去,山腰像裂开一条流火的伤口。狗吠、锣声、人喊混成一团,探照灯在林间乱扫,光柱偶尔掠过溪面,我潜入水下,只留鼻孔在外,数着心跳:一、二、三……灯柱移开的瞬间,我抬头,看见悬崖最高处立着一个人影——乱发翻飞,右臂无力垂着,是程述。她举着火把,像举着一面不肯倒的旗。隔这么远,我却仿佛听见她笑:跑啊,别回头!## 四
猴鸣与枪声再往前,溪谷渐宽,水声柔下来。岸边出现一排铁桩,上头悬着塑料桶——这是保护区给金丝猴补充盐分和矿物质的"舔食点"。我抓住铁桩,借力爬上碎石滩,腿一软,跪了下去。天边泛起蟹壳青,林子里传来"咯咯"猴鸣,像遥远的婴孩笑。我扯开猪尿囊,把菌粉倒进掌心,兑水吞下,再嚼半颗山椒。空胃被辣得痉挛,却也因此清醒——我不能昏在黎明前。就在撑地欲起时,"砰——"一声枪响划破山谷。子弹打进离我半米的湿沙,溅起泥花。我回头,看见麻贵带着三名村民顺索降追来,猎枪的火舌还在冒烟。"林小姐!"他喊,声音被山风撕得七零八落,"火是你放的?——回来,我让你做凤凰!"我抓起一把沙往他眼的方向撒,拖着腿滚下滩石另一侧。又是一枪,铁桩被击中,火星四溅,塑料桶"啪"地炸裂,白色盐粉漫天,像突降暴雪。我趁机钻进了矮杜鹃丛,枝叶带刺,划得脸颊生疼,却也给血迹做了掩体。## 五
断绳坡杜鹃丛后是一片风化页岩,当地人叫"断绳坡"——坡度陡,碎石松,连猴子都站不稳。我手脚并用往上爬,断腿使不上力,就用膝盖内侧卡石缝,像壁虎一样贴地移。身后脚步踩得碎石哗哗,他们越来越近。半腰处,我摸到一条废弃的监测绳——早期科研人员留下的钢芯尼龙绳,半段已悬空。我毫不犹豫把绳缠在腕上,借臂力把自己拖上去。绳芯刺破掌心,血顺腕流进袖口,我却觉得安全:疼在我身,命也在我身。登顶瞬间,我割断绳头,让整段绳带着碎石坠下。麻贵扑到崖底,只抓住空气,怒吼声在山谷来回撞,像困兽撞笼。## 六
雾里的迷彩天已鱼肚白,雾气自谷底升起,世界被调成灰白影调。我拖着腿继续北行,每一步都像踩在刀背。就在意识再次模糊时,前方雾幕里隐约出现两点荧光绿——迷彩服!我张嘴,却发不出声音——连日嘶喊、灌药、呛水,让我的喉咙像被砂纸磨穿。我踉跄冲过去,一头撞在那人胸口,手指死死抓住布料,用口型无声喊:"程——述——"对方明显一震,抬手示意同伴。另一名迷彩从背包取出保温毯裹住我,对讲机呼叫:"神农顶搜救组,发现幸存者,女性,腿部重伤,疑似失联游客。"我抓住第一名迷彩的衣领,用尽力气挤出嘶哑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:"麻湾......没有野人......是村子......拐卖......"他们互看一眼,神情瞬间凝重。领队蹲下来,目光笔直:"放心,我们带你回去,也会带人进去。"## 七
回声担架抬起那一刻,我回头望向来路——雾海翻涌,悬崖上的火光已弱成一条暗红丝线,却固执地悬在天际,像不肯熄灭的导火线。我把手腕上那块停走的表举到耳边——"哒——哒——"不知是因为体温,还是因为曙光,指针竟奇迹般开始挪动。我闭上眼,让晨光在眼皮上灼出一片通红。程述、沉塘、猴鸣、火鼓、尸体、辣椒、奶糖......所有碎片在血液里奔腾,汇成一句轰鸣:——我会回来,带着整个世界的光,接你回家。# 第五章
世界的光与影## 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