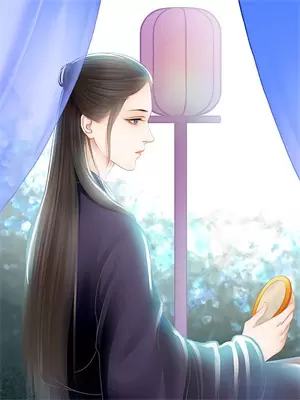1.车轮碾过最后一段硬化路面,猛地陷入林家坳村口的泥泞,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了脚踝。
我推开车门,一股浓稠的、混合着腐烂秸秆和潮湿泥土的气息猛地灌入鼻腔,
沉甸甸地压在胸口。村子静得可怕。记忆里夏日傍晚应有的炊烟、犬吠、孩童追逐打闹声,
全都死寂了。视线所及,多是泥坯房垮塌后的残垣断壁,野草在废墟间疯长,绿得发黑。
几缕稀薄的炊烟从零星烟囱里飘出来,没升多高就被沉甸甸的暮色压碎、扯散。
一种被遗弃的、死气沉沉的氛围,裹挟着南方梅雨季节特有的黏腻,紧紧贴在我的皮肤上。
我叫林晚。十年了,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故乡。目光不由自主地被村口那口老井吸过去。
它就蜷缩在老槐树巨大的阴影底下,井口压着一块巨大的青石板,
像是死死摁住了什么活物的咽喉。石板上刻满了扭曲的、我从未见过的符号,
深深凿进石头里,边缘被岁月和无数双手摸得光滑,却透着一股子邪性的冷硬。
井台周围寸草不生,泥地泛着一种不健康的苍白。这就是村里人口中那个“不干净”的地方。
小时候,太爷爷的烟袋锅子会重重敲在门槛上,厉声告诫我们这些娃娃,离那口井远点,
永远别靠近,更别想掀开那石板。一个佝偻的身影从旁边一栋低矮的土屋里挪了出来,
是赵老歪。他看见我,浑浊的眼睛像受惊的鱼猛地一缩,随即蒙上一层更复杂的情绪,
是警惕,甚至……是一点让人极不舒服的怜悯?“晚丫头?你……你咋这辰光回来了?
”他嗓子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。“奶奶病了,回来看看。”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,
心里却咯噔一下。这辰光?下午五点算什么特殊时辰?赵老歪的嘴角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,
像是想说什么,又硬生生咽了回去,最后只是重重叹了口气,摇着花白的头,
步履蹒跚地走开了,仿佛多在我身边待一秒都会沾染晦气。这种毫不掩饰的排斥,
像一根冰冷的针扎进心里。我拖着行李箱往家走,轮子在坑洼的土路上发出单调的噪音,
反而衬得村子更加死寂。偶尔有村民从门缝或窗后探出半张脸,眼神躲闪,一接触我的目光,
便像受惊的蜗牛,倏地缩了回去。压抑。像一张湿冷的牛皮,紧紧裹住了我。到家时,
爹正蹲在门槛上,脑袋埋在旱烟氤氲出的青蓝色烟雾里,看不清表情。听到动静,
他只是抬了抬眼皮,用烟袋锅子不甚耐烦地敲了敲地面。“回来了?屋里去,你娘在灶房。
”没有寒暄,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。这种刻意的冷漠,
比村口的寂静和村民的排斥更让我心寒。我把行李放进小时候住的房间,灰尘味浓得呛人。
简单擦了把脸,冰凉的水并没浇灭心头的郁结。我深吸一口气,准备去灶房帮娘做饭。
刚走到院子,脚步猛地钉在原地,血液仿佛瞬间冻结。
栓才能顶住的院门上——就在我眼皮子底下——用某种暗红色的、尚未完全干涸的粘稠液体,
画着一个巨大而扭曲的符号!那符号,和我刚才在村口井沿的石板上看到的,几乎一模一样!
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。鸡血?还是……?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炸开,直窜上天灵盖。是谁?
什么时候干的?我回来不到一个钟头,天色还未全黑,竟然有人敢摸到村长家门口,
干这种事!我强忍着恶心和恐惧,凑近细看。那符号的笔画狰狞狂乱,
边缘还往下淌着淡淡的血水,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腥气。这绝不是恶作剧。
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、充满恶意的警告,或者说……诅咒。“爹!娘!
”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发颤。爹从屋里出来,看到门上的符号,脸色瞬间阴沉得能拧出水。
他二话不说,转身从灶房舀来一瓢水,粗暴地泼在门上。水流冲淡了血迹,
符号变得模糊污浊,但那股不祥的、亵渎般的痕迹,却深深地蚀进了木头的纹理里。“没事,
哪个短命鬼瞎胡闹。”爹的声音干巴巴的,带着一种刻意压抑的暴躁,“回头找石灰粉刷刷。
”他试图轻描淡写,但他紧握烟袋锅、指节捏得发白的手,却出卖了他内心的震动。
娘从灶房出来,围裙上还沾着面粉,她看着门上那片狼藉,嘴唇哆嗦着,脸色煞白,
最终什么也没说,只是默默递给我一块干净的湿布。那一刻,我彻底明白,这不是偶然。
这个符号,和村子里弥漫的诡异死寂,和赵老歪那欲言又止的怜悯,甚至和爹娘异常的沉默,
都死死地缠绕在一起。夜色,像浓稠的墨汁,迅速渗透了林家坳的每一个角落。
我躺在硬板床上,院门上那个血红的符号,在我眼前灼烧。村口的古井,赵老歪的眼神,
爹娘的讳莫如深……所有碎片在我脑中疯狂旋转。就在意识模糊,
将被疲惫拖入睡眠的边缘时——嚓…嚓…嚓…一阵极其细微、却清晰得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,
穿透厚重的死寂,钻进我的耳朵。那声音,近在咫尺,就在院子外面。
像是……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,正一下,一下,坚持不懈地,刮擦着我家的木门板。
2. 无声的狗窗纸刚透进一丝青灰色的光,我就醒了。与其说是睡醒,
不如说是被一种黏在骨头缝里的寒意冻醒的。昨晚那湿漉漉的刮擦声,像一条冰冷的蛇,
盘踞在我脑子里,挥之不去。我轻手轻脚地起床,第一件事就是凑到窗边,
撩开厚重的土布窗帘一角,紧张地望向院门。门板上,昨晚被水泼过的地方,
留下一大片深色的水渍,边缘晕染开来,像一块难看的胎记。那个用血画的符咒模糊了,
但扭曲的轮廓依然顽固地嵌在木头纹理里,仿佛有了生命,正无声地嘲笑着我们徒劳的清洗。
院子里空无一人,只有晨雾像鬼魂一样,贴着地皮缓缓流动。一切安静得令人窒息。
我深吸一口气,推开门,想去灶房找点热水。冰冷的空气刺得鼻腔发痛。就在我迈出门槛,
右脚即将踩在潮湿的泥地上时,脚尖前的一幕,让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冲到了头顶,
又猛地褪去,留下彻骨的冰凉。门槛正前方,不到一尺远的地上,
整整齐齐地摆着三样东西:一撮乌黑油亮的水草,还带着河底的腥气;一小滩未干的淤泥,
颜色和井台边的一模一样;还有几根……灰黑色的、坚硬的动物毛发。是黑子的毛。
我养了八年的看门狗,黑子。它从不睡在屋里,夜里就卧在院门内侧,像个沉默的哨兵。
可此刻,狗窝是空的。一股巨大的、不祥的预感像铁钳一样扼住了我的喉咙。我猛地抬头,
视线疯狂地扫过寂静的院落。柴堆后?没有。水缸旁?没有。“黑子……黑子!
”我压着嗓子喊,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没有熟悉的奔跑声,没有欢快的吠叫回应。
我的心跳得像要炸开。我几乎是扑到院门前,颤抖着手想去拉开门栓,
看看它是不是跑出去了。可就在我的手触碰到冰冷木栓的前一秒,我停住了。
一种更深的恐惧攫住了我。我怕。我怕一开门,看到的不是活蹦乱跳的黑子,
而是……我猛地转身,冲回屋里,一把推开爹娘的房门。爹已经起来了,
正背对着我系外衣的扣子。娘还坐在炕沿,脸色比昨天更差。“爹!黑子不见了!
”我的声音带着哭腔。爹系扣子的手顿了一下,没有回头,
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沉闷的“嗯”。那声音里听不出丝毫意外,只有一种认命般的疲惫。
娘抬起眼,目光与我撞上,又迅速躲开,双手死死绞着衣角。他们的反应,像一盆冰水,
从我头顶浇下。他们知道。他们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“院门口……有水草,有泥,
还有狗毛!”我冲到他面前,逼视着他,“黑子到底怎么了?!”爹终于转过身,
脸上是那种熟悉的、试图掩盖什么的僵硬表情。“瞎嚷嚷什么!兴许是跑出去野了,
一会儿就回来。”“跑出去?门口那些东西怎么解释?昨晚那个刮门的声音呢?!
”我几乎是在吼了。“什么刮门声?你做梦了吧!”爹的音量也提了起来,
带着一种虚张声势的恼怒,“我看你就是城里待久了,神经过敏!赶紧洗把脸,
吃了饭该干嘛干嘛去!”又是这样。否认,回避,把一切归咎于我的“神经过敏”。
这种态度,比门外未知的威胁更让我感到绝望和愤怒。我死死盯着他,
一字一顿地说:“那不是幻觉。有人盯上咱们家了。黑子肯定出事了。
”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,嘴唇动了动,最终却什么也没说,只是粗暴地推开我,
径直走向灶房。那一刻,我清楚地感觉到,我和这个家之间,隔着一层厚厚的、冰冷的墙。
墙那边,是父母拼命想要隐藏的秘密;墙这边,
是我这个被排除在外、独自面对恐惧的“外人”。我没吃早饭。
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房间里,听着灶房传来碗筷碰撞的单调声响,心里一片冰凉。
黑子不见了,连同它一起消失的,似乎还有这个家里最后一点安全感。不知过了多久,
我听到院门被打开又关上的声音。是爹出去了。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决定跟出去看看。
我需要知道黑子的下落,哪怕是最坏的结果。我悄悄溜出院子,
远远看见爹的背影正朝着村后那片荒废的河滩地走去。他手里似乎拎着个什么东西,
用破麻袋裹着,看起来沉甸甸的。我的心猛地一沉。那个形状……那个大小……我屏住呼吸,
借着半人高的荒草和残垣断壁做掩护,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。脚下的路越来越荒凉,
河水的腥气也越来越浓。爹在一处远离村舍、长满芦苇的河湾边停了下来。
他四下张望了一番,确定没人后,弯下腰,开始用手刨坑。泥土飞溅,
他的动作带着一种急躁和……恐惧。我躲在一丛茂密的芦苇后,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。
他到底在埋什么?坑挖得差不多了。爹直起身,喘了口气,然后弯腰去拿那个破麻袋。
就在他掀开麻袋一角的那一刻,我看到了——一抹熟悉的、灰黑色的皮毛!是黑子!
它僵硬地蜷缩着,脖子以一个极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,眼睛瞪得溜圆,
空洞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。它的嘴里,塞满了湿漉漉、脏兮兮的水草!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,
才没有尖叫出声。眼泪瞬间涌了上来,不是因为悲伤,而是因为一种彻骨的愤怒和恐惧。
他们杀了黑子!或者,他们知道是谁杀了它,却在偷偷掩埋证据!
爹匆匆将黑子的尸体推进土坑,飞快地填上土,又拔了些芦苇盖在上面。做完这一切,
他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,在原地站了很久,才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。我等他走远了,
才从芦苇丛后走出来,双腿发软地走到那个小小的土堆前。
新鲜的泥土气息混合着河水的腥臭,令人作呕。黑子死了。不是意外,是警告。
是针对我的警告,还是针对我们全家的?爹为什么要隐瞒?他到底在怕什么?我蹲下身,
手指深深插进冰冷的泥土里,浑身止不住地颤抖。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,
突然变得如此陌生而危险。每一寸土地,每一张面孔,似乎都隐藏着秘密。
我必须弄清楚真相。不能再指望父母了。我要靠自己。正当我准备起身离开时,
眼角的余光瞥见旁边一丛被踩倒的芦苇上,沾着一点暗红色的、已经干涸的痕迹。不是泥。
是血。血迹旁,半个模糊的脚印,清晰地印在松软的河滩上。那脚印的大小和纹路,我认得。
是堂叔林老栓的解放鞋。一股寒意,比河水更刺骨,瞬间沿着我的脊椎爬满了全身。
刮擦声再次在我脑中响起,这一次,无比清晰。它刮掉的不是门板上的漆,
而是这个家看似平静的表面,露出底下血淋淋的真相。3.祠堂暗影堂叔林老栓的解放鞋印,
像一枚烧红的烙铁,烫在我的视网膜上。河滩的冷风刮过,我却觉得浑身血液都在嗡嗡作响,
愤怒和一种被背叛的寒意交织在一起,几乎要冲垮理智。他为什么要杀黑子?
爹为什么要替他隐瞒?那口井,那个符咒,到底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,
需要用到这种灭口牲畜的残忍手段?我不能等。不能再指望任何人。
黑子的死像最后一道催命符,逼着我必须做点什么。一整天,我把自己关在屋里,
强迫自己冷静。爹回来时,身上带着河滩的泥腥味,眼神躲闪,绝口不提埋狗的事。
晚饭桌上,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。娘机械地扒着饭,眼窝深陷。
爹则一杯接一杯地灌着劣质的散装白酒,仿佛想用酒精溺死心里的不安。我什么也没问。
我知道,问不出任何结果。这个家,已经用沉默砌起了一堵高墙,把我隔绝在外。
夜幕再次降临,比前一天更沉,更死寂。窗外连风声都没有,
整个林家坳像被塞进了一个巨大的、密不透风的棺材里。我躺在床上,睁着眼,等待。
等待家里最后的灯火熄灭,等待爹娘的鼾声响起。时间像生锈的齿轮,缓慢地转动。
当月光透过窗棂,在地上投下惨白格子时,我悄无声息地溜下床,
摸出早就准备好的手电筒和一把小巧却锋利的水果刀。我的目标,是村东头的林家祠堂。
那里是林家坳存放族谱、记载过往的地方。也是奶奶日记里,
隐约提及可能与沈春娥之死有关的地方。如果有什么秘密被刻意抹去,
祠堂或许会留下蛛丝马迹。推开房门,冰冷的空气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。
院子里的每一处阴影,都仿佛藏着东西。我紧握着水果刀,指甲掐进掌心,
用细微的痛感强迫自己镇定。祠堂离我家不远,但这段路,我却走得如同跋涉刀山。
每一步落地都轻得不能再轻,耳朵竖着,捕捉着任何一丝异常的声响。远处,
那口古井沉默地蛰伏在槐树阴影下,像一只窥伺的眼睛。祠堂的木门没有上锁,只虚掩着。
一股陈年的灰尘和霉味扑面而来。我侧身挤了进去,反手轻轻带上门。手电光柱划破黑暗,
照亮了布满蛛网的梁柱和层层叠叠的牌位。那些黑漆漆的木牌,在光线下反射着幽光,
像无数双冷漠的眼睛,注视着我这个不速之客。心脏在胸腔里狂跳。我凭着儿时模糊的记忆,
摸索到存放旧箱笼的角落。那里堆着一些早已无人问津的杂物和旧文书。
灰尘呛得我直想咳嗽,又拼命忍住。我跪在冰冷的地上,开始小心翼翼地翻找。
手指很快变得乌黑,蛛网粘在脸上,又痒又恶心。但我顾不上了。
账本、地契、泛黄的生产队记录……大多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
焦虑和失望开始蔓延。难道我的判断错了?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,
我的指尖触碰到箱底一个硬硬的、边缘粗糙的东西。不是纸,更像是一本……皮面的笔记本?
我把它抽出来,掸去厚厚的灰尘。封皮是深褐色的,没有任何字样,
但摸上去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滑腻感。像是……被汗手反复摩挲过。深吸一口气,
我翻开了它。纸页泛黄发脆,字迹是钢笔写的,有些潦草,却力透纸背。开篇的日期,
是近四十年前。“……七月半,鬼门开。井里的响声又大了,像是有东西在下面撞石头。
爹说不准提,不准看,可我怕……”我的呼吸骤然屏住。这是谁的日记?我快速向后翻,
心脏越跳越快。日记断断续续,记录着一些零碎的生活琐事,
但总绕不开那口井和村里的压抑气氛。直到我翻到中间一页。“……春娥姐走了。
他们说她是自己投的井。我不信!前天她还跟我说,等秋收卖了粮,
就扯布做新衣裳嫁人……她怎么会……而且井口那块石板,两个后生都抬不动,
她一个人怎么掀得开?!”字迹在这里变得激动而混乱,大片墨渍晕染开来,
仿佛写字的人当时在剧烈颤抖。“……夜里偷偷去看,
井沿上有抓痕……很深……像是被什么东西硬拖下去时指甲抠出来的……还有半枚扣子,
是春娥姐衣裳上的……他们都在说谎!”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。后面几十页都是空白。
仿佛有一桶冰水,从我的头顶浇下,四肢百骸瞬间冰凉。沈春娥不是自杀!
她是被……她是被拖进井里的!四十年前,有人在井边杀了她,并制造了自杀的假象!
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我的脑子。是谁?日记的主人是谁?他她后来怎么样了?
为什么日记会藏在这里?巨大的恐惧和震惊让我浑身发抖。我猛地合上日记,
想把它塞回原处,手指却碰到日记本封皮内侧一个硬硬的突起。我捏了捏,
里面似乎夹着什么东西。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挑开缝合线,从封皮的夹层里,
我抽出了一张折叠得小小的、已经脆化的纸片。展开纸片。上面用毛笔,
画着一个极其复杂、我从未见过的符咒。比井沿上和门上的,都要繁复、诡异百倍。
符咒下方,有一行小字,墨色暗红,仿佛干涸的血:“封井咒。以血为媒,魂镇百年。
妄动者,祸及子孙。”我的手一抖,纸片差点飘落。血咒?魂镇?这口井里,到底镇着什么?
需要用到这么恶毒的东西?而沈春娥的死,和这个血咒,又有什么关系?难道她的死,
本身就是……仪式的一部分?!这个想法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般的恶心。
就在这时——“吱呀——”祠堂那扇厚重的木门,被人从外面,缓缓地推开了。
一道被月光拉得极长、极扭曲的影子,慢慢地爬进了门槛,无声地向我延伸过来。
一个佝偻的身影,堵在了门口,背对着月光,面目模糊不清。只有他手里提着的那把东西,
在惨淡的光线下,反射出一点冰冷的、金属的寒光。像是一把……砍柴刀。
4. 井底窥影祠堂那扇厚重的木门,在死寂里发出令人牙酸的“吱呀”声,缓慢地被推开。
一道被惨淡月光拉得极长、极扭曲的影子,像粘稠的墨汁,一点点爬过门槛,
无声地向跪在地上的我蔓延过来。冰冷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,血液仿佛冻结。
一个佝偻的身影堵在门口,背对着门外稀薄的月光,面目模糊不清,
只有轮廓依稀可辨是堂叔林老栓。他手里提着一把砍柴刀,
粗糙的刀身在微弱光线下反射出一点冰冷、死寂的寒芒。空气凝固了。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,
和自己心脏在耳膜里疯狂擂鼓的声响。“晚…晚丫头…” 林老栓的声音沙哑得厉害,
像砂纸在生锈的铁片上摩擦,“你…你不该来这…更不该…翻这些东西…”他向前挪了一步,
柴刀刀尖拖在地上,发出“刺啦”的轻响,在这绝对的寂静中,清晰得骇人。
我闻到了他身上那股浓重的、混合着汗臭和河底淤泥的腥气。
我猛地攥紧手里那本日记和血咒纸片,手心里的冷汗几乎要将它们浸湿。我强迫自己站起来,
双腿却软得不听使唤,只能靠着身后冰冷的供桌。“栓子叔…”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,
“黑子…是不是你杀的?赵老歪…是不是也是你们…”“闭嘴!”林老栓突然低吼一声,
声音里带着一种困兽般的绝望和疯狂,“你知道什么?!都是为了这个村子!为了活下去!
”他又逼近一步,浑浊的眼睛在黑暗里死死盯着我,
里面翻滚着我从未见过的混乱和恐惧:“那口井…那下面的东西…不能出来!谁想动,
谁就得死!这是规矩!老辈传下来的规矩!”“规矩就是用活人填井吗?!
”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,扬了扬手里的日记,“沈春娥是不是你们害死的?!用她的命镇井?
是不是!”听到“沈春娥”三个字,林老栓的脸剧烈地抽搐了一下,像是被无形的鞭子抽打。
他举起了柴刀,刀尖指向我,手却在微微颤抖。“你懂个屁!”他嘶喊着,唾沫星子飞溅,
“没有她…没有镇着…林家坳早就没了!我们都得死!现在咒松了…它饿了…得喂…得喂啊!
”他的话语颠三倒四,充满了非理性的疯狂。但我听懂了一点——井里的东西,需要活祭!
而他们,一直在用这种残忍的方式“喂养”它,维持着一种扭曲的“平衡”!
“所以…所以黑子…赵老歪…”我感到一阵反胃的恶心。
“不够…都不够…”林老栓的眼神涣散开,喃喃自语,
“它要的是…是林家嫡系的血…女的…阴气重…最补…”他的目光,像毒蛇一样,
骤然钉在我脸上。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头顶。我瞬间明白了。我回来,
正好撞上了他们的“献祭周期”!而我,
这个林家嫡系的、刚从外地回来的、带着“生”气的女儿,成了他们眼中最完美的…祭品!
恐惧和愤怒像火山一样在我胸腔里爆发。我不能死在这!就在林老栓眼神一狠,
挥刀作势要扑上来的瞬间,我猛地将手里的日记本狠狠砸向他面门!灰尘弥漫,
他下意识地闭眼格挡。就是现在!我像兔子一样从他身侧的空隙窜了出去,